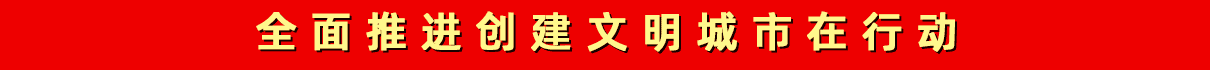当前位置:安徽生活都市网 >> 网友原创 >> 文章正文
张猛对《记忆记忆》-俄罗斯历史记忆谜题的评论

《记忆记忆》,[俄]玛利亚斯捷潘诺娃,李春雨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2020年11月出版,432页,78.00元
小时候,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决定为她的家人写一本书。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小学作业本上写了五六页的家族史。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个项目从未搁浅过。她收集信息,走访祖先定居的偏远城镇,直到《记忆》这本书定稿。
斯捷潘诺娃写作的初衷是个人的:它来自个人对整个家庭的使命感。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她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野心,用她的话说,这是“对20世纪的一种诠释”。从这个《记忆记忆》的呈现状态来看,斯捷潘诺娃找回的过去的记忆是凌乱的,有一种玻璃破裂带来的震惊和恐慌感。从不同角度看那些碎片,可以看到被反射物体的不同侧面。极度困惑和震惊,也许这也是一个模仿记忆本身中多色调面孔的实验。支持实验结果的实验参数不仅包括叙述者丰富的祖先,还包括20世纪俄罗斯神秘多变的历史。
全书开头的第一句话相当简单。这些话确立了整本书的调性。作者想通过追溯“记忆”来重新解读“死亡”;以回忆的名义还原时代的乡土气息。然而,这些回忆的话语与死者的真实经历究竟有多远,抑或只是斯捷潘诺娃单方面与死者发起的“对话”?这些自然是无法验证的。作为一名诗人,斯捷潘诺娃的诗歌风格极其独特,几十年来她对“家庭记忆”这一主题的执着思考也使她的写作变得复杂,许多想法凝结成了具有鲜明色彩的个人想法(这也是这本书难以阅读、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看完这本书,我不禁想到,也许家族史是斯捷潘诺娃的幌子,她想通过“写家谱”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这些丰富多样的观念交织在家庭成员和历史人物之间,仿佛构成了通向神秘花园的交叉路径。
恋物:日常器具的神圣之光
斯捷潘诺娃为他的回忆过程列举了数百件旧物,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作为书封面的破瓷娃娃。这些瓷娃娃最初只是为了减少材料运输过程中的碰撞而生产的,几十年来一直是商店里流行的装饰品。不完整使它们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本书的核心隐喻。为了节约成本,这些名为“夏洛特冰人”的瓷娃娃在粗加工时只在一面上釉,被时间意外地涂上了一层神圣的光,仿佛日本浮世绘作为瓷器的包装纸被带到了欧洲,影响了印象派的绘画理念。附着在物体上的记忆增加了它的魅力。在这篇文章中,斯捷潘诺娃还触及了她隐居的姨妈的另一面,她在整理自己凌乱的遗物时特立独行。作为日常用具的旧东西构成了整个历史的细节。
还讨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老照片作为记忆的证明。斯捷潘诺娃用一章的篇幅细致地描述了他手上的20张旧照片。——是文字描述,而不是直接把照片插入书中参考。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她否定了照片对于记忆保存的权威性意义。斯捷潘诺娃对摄影(包括纪实摄影)的态度是消极的。她不相信镜头下的瞬间,认为它们阻碍了触及生活的本质。包法利夫人第一次体验摄影时,忍不住惊呼:“这就是我。”然后,从三十六张照片中,她选择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然而,与肖像所追求的“相似性”相比,斯捷潘诺娃认为照片的刻板和真实的复制是相当不可抗拒的,“照片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对真实事物的保存”。
“照片先讲究变化,一次又一次地成长、繁荣、衰落、消亡.艺术从事的是相反的事情:任何成功的文字库都是关于成长的里程碑,并不完全符合第一条皱纹或者黄褐斑的出现。照片细致入微: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很快会不复存在,所以要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一切。”
在这里,斯捷潘诺娃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表面上最忠诚的形象,最终可能离真理最远。这部分的讨论,很可能会把痴迷于拍照修图的当代读者置于尴尬的境地。现在有太多的人痴迷于“理想化摄影”,迫不及待地要出门戴上一副具有过滤功能的眼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捷潘诺娃声称,由数字技术产生的大量机械复制图片最终将进入“另一个墓地”,这是一个最终被遗弃的巨大图像垃圾场。相比较而言,她肯定了摄影师拍照时的疏漏,比如“狂欢节丝绸服饰下的丑鞋”,至少他们忠于自己的时代。
日记与信件:暧昧多义的
记忆存储库除了对当事人曾经使用过的器物进行考察,斯捷潘诺娃还把记忆挖掘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上面。从姑妈留下来的黑色日记本开始,斯捷潘诺娃开始借助家族成员的文字进行知识考古。不过,她并不认为这些文字都是可信的,她判断的依据是写日记的人是否构想了一个“潜在作者”。斯捷潘诺娃据此将日记分成了两类:具有特定阅读对象的“表演性日记”,以及为了个人量身打造的私密性日记,外人很难进入。姑妈的信带给她的是后一种感受,那些事无巨细的清单罗列像宽眼渔网一样,留下了本人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留给自己。
日记对于访客或许是封闭的,而信件则尽可能地敞开了语义丰富的大门。这些信件里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二战期间发自列宁格勒战场的几封家书。作家外祖父的姨弟廖吉克由于征兵年龄的变更,十九岁便参加二战,并随着队伍四处迁移。像普遍的战争文学那样,廖吉克在信里向家人传达爱国的热情,分享战场上的喜悦,但他在负伤后也会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向家里人诉说想家的苦闷。或许那些文字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斯捷潘诺娃在文中引用了书写“列宁格勒大围困”的作家利季娅·金斯堡的说法,二战以及“列宁格勒大围困”使得个性特征消失,个体的人变成了群体的“死者”。而她的这些追溯将廖吉克从万千死者的队伍里推了出来,使一段近乎遗失记忆重新被发现,被更多人读到。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信件,穿插在第一、二部分的章节之间,构成了举足轻重的“插章”。这些通信大都与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太姥姥萨拉·金兹堡有关。萨拉·金兹堡曾远赴巴黎学医,从世界著名的医学院毕业。少女时代她受到革命思想鼓舞,曾参加1905年下诺夫哥罗德的街垒战,后来由于散发非法传单被捕。她与后来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曾经是同学,也数次在政治劫难中幸免,像足够幸运的“瓷娃娃”一样得以保全。斯捷潘诺娃选取了她与太姥爷“桑丘·潘沙”之间的通信作为“插章”,这些信件沿着两条线行进:个人层面上的学业、生活、男女情感,以及公共层面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对时局的评价。这些进入到记忆存储库的信件材料是有趣的,它或许不过是革命年代里的“大众叙事”,但放在今天的语境里,以我们的“经验”去触摸革命理想主义的文本,会明显感受到记忆暧昧多义的一面。
故地重游,寻找记忆花园的坐标
斯捷潘诺娃在书中提到自己华盛顿的一位历史档案学者交谈时,称自己是如今非常流行的、热衷于寻根之旅的游客之一。事实上,她的寻根之旅比泛泛意义上的游客要全面丰富许多。在筹备这本书的三十五年时间里,她沿着祖先走过的路途去了很多地方:为了更多地获取沉默的家族的隐秘,她走过波钦基的羊肠小道;为了更近地感受到太姥姥当年的心境,她专程造访过萨拉一个世纪以前在巴黎住过的旅馆;为了寻找记忆更深远的源头,她只身前往祖太姥爷的故乡敖德萨……事实上,这些地理坐标也都和俄罗斯历史的不同侧面有隐秘的联系,斯捷潘诺娃的寻根之旅带着一枚俄罗斯历史的罗盘。
寻访的过程有些类似于悬疑小说的情节,但很少有“水落石出”的结局抚慰旅途的劳顿。在赫尔松市的档案局,她从文件中获知祖太姥爷曾经一手操办铸钢厂、铸铁厂、机器制造厂,也从1918年的工厂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中,读到古列维奇私人财产移交至工厂工人所有的决议,甚至从普遍的历史文献中了解到1917-1920年间赫尔松经历的政权更迭、社会变动,但关于祖太姥爷个人的命运,她却没能够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具体的“人”的形象被隐没了,只有博物馆里一台庞大的、配件完整的犁具还耸立着,机身的大写基里尔字母“古列维奇卡霍夫卡工厂”,证实祖太姥爷的家族确实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通过故地重游重建历史形象,这是一种精准的考古,还是个人主观情感的附会,在斯捷潘诺娃笔下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在友人的带领下,她来到位于萨拉托夫的外祖父的旧宅院。院子里的一切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心灵相通,“我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纤维毕现地还原了家族当年在此地的生活:他们如何在此地居住,又为何离开这里。院子将我抱在了怀里”。然而,此后不久,朋友却打电话告诉她,上次搞错了,他们去的并非外祖父的宅院。这段经历对所有试图找回记忆的人,都构成了一次拷问:我们真的是在忠实地保存自己的记忆,还是被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力量裹挟着“编排记忆”?
“同时代人”:家族记忆的“大历史”视野
单纯写家族成员的命运不会是斯捷潘诺娃的落脚点。在她包罗万象的追溯中,家族的记忆从纯粹私人的空间跳脱了出来,她将追忆的范围扩大到与自己的祖辈同时代的世界文化名人身上,大量的历史史实与家族成员间的命运遭际相互交织缠绕,作为参考的“同时代人”,构成了通往二十世纪记忆花园的另一条幽暗的入口。
譬如,从作品内页的家族人物图谱可以看到,斯捷潘诺娃的祖先们来自于斯捷潘诺夫、金兹堡、弗里德曼、古列维奇,而这些姓氏中有三个都属于犹太人。在追溯记忆的过程里,斯捷潘诺娃也曾经多次提到犹太人的历史境遇问题,这个二十世纪人类记忆绳索上的一个死结。从太姥姥寄往家中的明信片和信中对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信息讳莫如深,到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库兹明、勃洛克等人对曼德尔施塔姆犹太身份的揶揄,犹太人的种族问题像一条充满耻辱的尾巴一样,被藏在了俄国主流文化的背后。不仅如此,斯捷潘诺娃还在世界各地拜访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寻访那些文化名人的踪迹,如遭到纳粹迫害的夏洛特·萨洛蒙、安妮·弗兰克等,在一阵虚妄的冲动驱使下,她甚至希望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拯救湖里那些“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的头颅。现实生活里,那被驱逐、被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以至于斯捷潘诺娃的父亲得知自己当年的家书要被发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祖辈们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遭遇的无妄之灾,教给了他们韬光养晦的哲学,斯捷潘诺娃却勇敢地向人暴露伤疤,她试图重整这些惨烈的记忆,恢复自己的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应有的地位。
俄罗斯评论家将这本书称为“世界之书”,这主要是就它宽广的写作视野而论。斯捷潘诺娃担任了多年文艺网站的主编,平日阅读面十分庞杂。她身上具有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特质,对世界文化如数家珍,这从译者在正文后附上的两百多条注释就可以看出来。斯捷潘诺娃在与故去的家庭成员对话,也在和世界文化名人进行观点的沟通,赛巴尔德、曼德尔施塔姆、拉斐尔·戈德切恩、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夏洛特·萨洛蒙等等文化符号,被同一根线串了起来:究竟什么是记忆?应当怎么去看待人类的记忆。尤其是在那些形成巨大历史分水岭的事件之后,应该怎样讲述所谓的“后记忆”?
在具有非虚构特征的散文集《时代的喧嚣》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追忆了自己和同时代人的过去。斯捷潘诺娃认为,他的目的是将过去“盖棺定论”,归根结底“排斥记忆”,而这是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不能认同的。他的朋友茨维塔耶娃也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她以丈夫的白卫军形象为傲,曾经写过多首诗歌献给心目中的“骑士”。她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诋毁了白卫军,因此在多个场合对他进行批判——她要拥护的“记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斯捷潘诺娃借此对记忆的客观性再次提出质疑。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让家族记忆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模糊了边界,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剖面。
作为本书中心人物的太姥姥萨拉·金兹堡,和“瓷娃娃”一样,是历次劫难的幸存者之一。过往的经历塑造了她,使得晚年的她显得极其干练,“山岩一样”,“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在斯捷潘诺娃留存下来关于她的记忆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萨拉·金兹堡喜爱在钢琴旁弹琴唱歌,她最后一次天鹅遗曲般的歌唱,选择的竟然是青春时代低沉而悲壮的《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当那激动的嗓音从她衰老的躯体里涌出时,“身陷布特尔斯基监狱的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手持《爱尔福特纲领》的中学生曼德尔施塔姆、雅尔塔革命者集会上的十三岁的茨维塔耶娃”——所有太姥姥同时代的年轻人奏响了一曲合唱,宣布要与旧世界决裂。通过种种记忆的拼贴,斯捷潘诺娃再次试图扩大家族记忆的范围,所有相互交叉的小径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整个二十世纪诡谲多变的文化与历史。